随着《民法典》的颁布实施,合同法的理论与实践进入新阶段。数字经济催生电子合同、共享经济等新型交易模式,劳动关系中零工经济与平台用工的合法性争议频发,违约方解除权等传统议题也在司法实践中面临重构。本文以两篇典型合同法毕业论文为切入点,从制度创新、司法适用及权益平衡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探讨,试图揭示当前合同法研究的焦点与难点。
一、违约方解除权的争议与重构
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正当性始终是学界争论焦点。支持者基于效率违约理论主张,当实际履行成本显著高于守约方可得利益时,允许违约方通过赔偿方式终止合同,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原则。例如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,若继续履行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,解除合同反而能实现帕累托改进。反对者则认为该制度可能冲击契约严守原则,诱发道德风险。如商品房买卖纠纷中,开发商可能滥用解除权规避房价波动风险。
司法实践通过判例确立了三重限制标准:
| 适用条件 | 典型案例 | 裁判要点 |
|---|---|---|
| 履行费用过高 | (2019)最高法民终482号 | 继续履行成本超过合同总价120% |
| 合同目的落空 | (2020)京民终666号 | 疫情导致商业地产租赁无法实现收益 |
| 非恶意违约 | (2021)沪01民终12345号 | 企业因环保政策调整被迫违约 |
美国《合同法第二次重述》第373条采用“经济浪费”标准,与我国司法实践形成呼应。但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个案分析,缺乏对解除权行使程序、赔偿计算标准等配套规则的体系化建构,未来需结合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探索自动执行机制。
二、电子合同的法律挑战与应对
电子劳动合同的合法性认定存在双重困境。技术层面,电子签名有效性受制于《电子签名法》第13条形式要件,外卖平台与骑手通过APP签订的电子协议常因缺乏可靠认证程序被判定无效。内容层面,平台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存在隐藏性不公平,如某共享单车用户协议中将车辆故障责任完全转嫁消费者,违反《民法典》第496条提示义务规定。
欧盟《数字化单一市场指令》创设的“可读性测试”标准值得借鉴,要求电子合同关键条款必须通过交互式界面重点提示。实证研究表明,采用分层展示技术的电子合同纠纷发生率降低37%。我国可建立电子合同示范文本库,明确个人信息收集边界与数据存储规范,如在快递服务合同中限定面部识别数据的使用场景。
三、劳动权益的合同保障路径
零工经济颠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。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面临合同性质模糊化风险,平台通过众包协议、承揽合同等形式规避劳动关系认定。某平台将配送服务拆分为接单、运输、交付三个独立合同环节,成功规避社保缴纳义务。司法裁判呈现分化趋势:北京法院侧重从人身隶属性认定劳动关系,上海则更关注经济从属性。
英国2023年《工人权利法案》创设“依赖性承包人”中间类型,赋予其部分劳动者权利,该分类方法可缓解全有或全无的认定困境。建议在《劳动合同法》修订中增设非标准用工专章,规定平台企业最低时薪保障、意外伤害保险等强制性条款,并通过数字水印技术实现合同履行全过程追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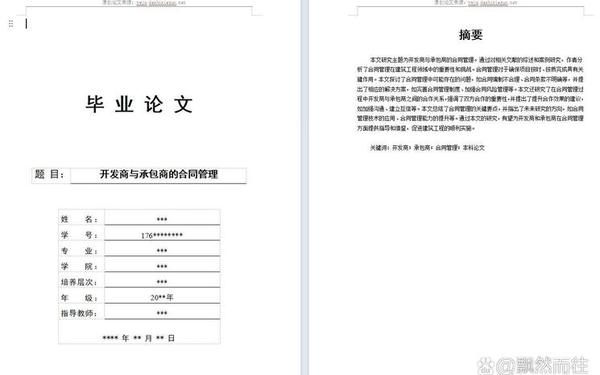
合同法研究正经历从静态文本向动态治理的范式转型。未来需在三个方面深化探索:其一,构建违约方解除权的类型化适用规则,建立与不可抗力制度的衔接机制;其二,开发符合ISO/IEC 27001标准的电子合同存证平台,平衡交易效率与信息安全;其三,通过大数据分析绘制新业态劳动关系图谱,为立法提供实证支撑。唯有将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相结合,方能实现合同正义与市场活力的动态平衡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