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秋的月亮总是圆的,可人心却未必能圆满。那年的月夜,我踩着满地银辉推开家门时,正听见爷爷用竹筷敲着瓷碗,对着一桌冷掉的饭菜吟诵: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他佝偻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,像是枯枝上最后一枚摇摇欲坠的叶。
一、缺席的团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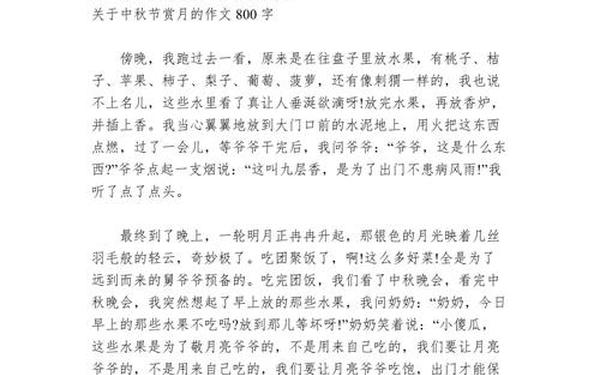
父亲在青藏高原架设信号塔的第三个中秋,母亲总把月饼切成六等份。“你爸那份放冷冻层,等他过年回来吃。”她将冰皮月饼递给我时,指尖沾着细碎的冰晶。阳台上那株移植自老家的金桂开得正盛,香气却裹着苦涩——去年爷爷执意要挖来城里时,奶奶曾拽着树根哭喊:“挪了根的树活不长的!”此刻桂花瓣簌簌落在爷爷的白发间,倒像是撒了把盐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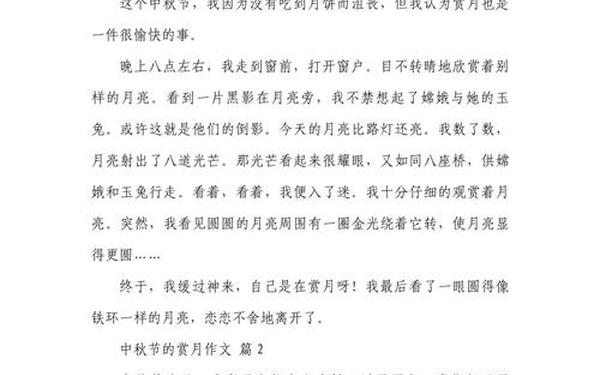
二、月下的诗行
“咱们来飞花令,带‘月’字的!”爷爷突然起身,布满老年斑的手掌拍在石桌上。他先诵了句“海上生明月”,母亲接“明月松间照”,我卡在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,却瞥见母亲悄悄用手机查诗句。夜风掠过防盗网的缝隙,将搜索页面吹成晃动的光斑,像极了老家溪涧里跃动的银鱼。爷爷忽然仰头大笑:“当年你奶奶不识字,偏要接‘月亮走我也走’,气得私塾先生摔了戒尺!”月光忽然漫过他湿润的眼角。
三、生根的月光
零点钟声响起时,父亲的视频请求从雪山顶峰传来。屏幕里的月亮大得惊人,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塞进行李箱。“这里的月亮比老家亮三倍!”他呵出的白雾模糊了镜头,身后是呼啸的风雪。爷爷突然凑近手机喊:“把月亮掰半块回来!”所有人都笑了。阳台上那株金桂忽然抖落一地花瓣,在月光里翻飞如迁徙的蝶群——原来有些牵念,早就在水泥森林里扎了根。
【后记】后来父亲带回一罐高原月光(他说是雪水),浇灌的金桂竟在腊月结了花苞。如今每当中秋,我们仍会在月下读诗,只是瓷碗里盛的不再是残羹冷炙,而是从冻土层苏醒的春天。或许最圆的月亮,本就不是挂在天上,而是住在愿意为你留一盏灯的人心里。

